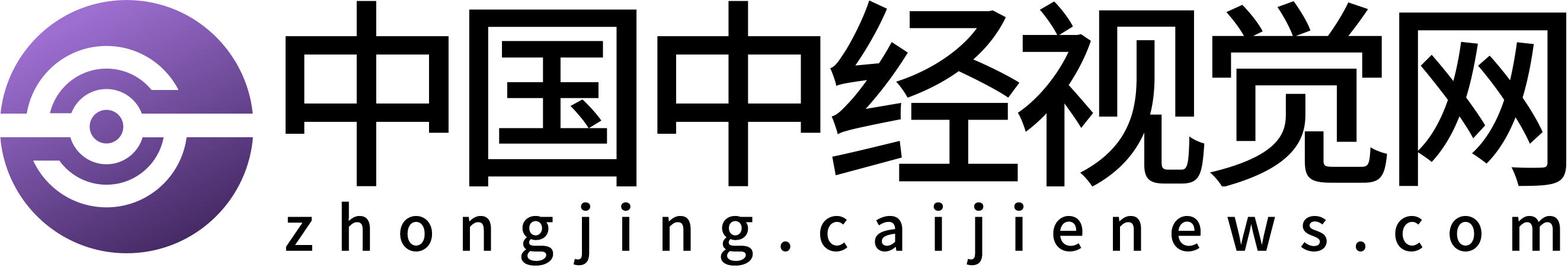特稿|三星堆印记
2023年7月27日,备受瞩目的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开馆,展陈数达原展出文物的3倍之多,新一轮考古中早已为公众所熟知的文物青铜神坛、骑兽顶尊人像、龟背形网格状器、虎头龙身像等重器尽数亮相。
三星堆遗址距今4500年至2900年,是迄今长江流域规模最大的商时期古蜀国都城遗址,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发展格局的重要见证,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以来,新发现的3—8号祭祀坑出土各类文物17000余件,三星堆古蜀人留下的印记“再醒惊天下”。
图说: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新民晚报记者 姜燕供图(下同)
 【资料图】
【资料图】
追溯
四川德阳广汉鸭子河畔的三星堆遗址,许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
上一次是37年前,1986年因附近的砖瓦厂发现玉石器和青铜器,由此启动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1、2号祭祀坑出土的大量稀世之珍神秘而瑰丽,高达3.96米的青铜神树、高2.61米的青铜大立人、宽1.38米的青铜纵目面具,以及流光溢彩的金杖等金器曾震惊了世界。三星堆“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
在此之前,更要追溯到1927年春季的一个傍晚,四川广汉月亮湾的村民燕道诚和儿子燕青保在自家门口不远处挖水沟,为农耕做准备,燕青保用锄头翻起泥土时,忽然被一件硬物震得手疼,刨开一看发现是块玉石器。这一锄敲开了尘封3000年的古蜀国大门。
1934年春,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馆长、美籍教授葛维汉征得四川省教育厅与广汉县的同意后,对月亮湾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也发现了一些玉石器。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学家冯汉骥与王家祐曾几次前往广汉考察,他们推断三星堆与月亮湾一带遗址密集,很可能是古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唐朝诗人李白的《蜀道难》,为传说中的古蜀历史抹上了一层浓郁的神秘色彩。
早在远古时期,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和四川盆地就已经是古蜀先民的栖息之地,到了夏商周时期,古蜀国已成为西南地区的富庶之地,但由于传世文献对古蜀早期历史的记载非常模糊,一直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
“一醒惊天下”之后,三星堆逐渐从惊艳的目光中淡出,带着它的无数未解之谜,静静地等候在中国西南一隅。
图说:青铜大立人
开坑
2019年12月的一天,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在“1、2号祭祀坑”周边系统考古勘探中,一件青铜器的一角意外被发现。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队领队雷雨说,大家原来都不相信还有新坑,只能说试着挖挖。2019年12月2日,当考古人员不抱太大希望地在1、2号祭祀坑周围小规模试掘时,意外找到一处坑状遗迹,而在这座坑内发现了绿色的青铜器。大家满心疑惑这件青铜器属不属于三星堆文化,首任三星堆考古领队陈德安下坑伸手一摸,凭借深厚的经验,斩钉截铁地说:“是大口尊,没问题!”
雷雨说,陈老师说是大口尊之前,他都觉得完全可能是宋代的铜器,后来才认识到,必须得承认还真有3号坑。
这次考察,基本摸清了“1、2号祭祀坑”周边祭祀区域的范围和各类遗存的年代序列和空间格局,新发现了6座祭祀坑。1986年发掘的1号坑和2号坑之间,约30米,最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就位于这30米之间。
雷雨说,21世纪的前十年做过两次密集探测,遗憾的是2004年以后为了展示1、2号坑,做了一个平台,刚好把这几个坑完全遮盖住了,仅有3号坑的角落露出在外面。这次刚好把这个角给找着了。
“不然的话,又得等几代人吧。”雷雨说。
虽然并不知道地下还埋藏着什么宝贝,但曾经“一醒惊天下”的三星堆带给人无限遐想。2020年9月6日上午,“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2020)启动仪式”在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大棚内举行。时隔34年,三星堆遗址发掘再次启动。
图说:青铜纵目面具
幸运
三星堆祭祀区重启发掘受全国考古界瞩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选择了开门做研究,邀请全国33家学术机构深度参与考古发掘、文物保护与课题研究。在现场忙碌的,是一个包括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环境考古、地质考古、冶金考古、文物保护技术、体质人类学、材料科学等在内的多学科交叉创新研究团队。
考古发掘工作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上海大学、四川大学等相关高校的团队前往助阵,文物清理、修复团队不乏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等重量级修复师的身影,全国著名文保专家、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研究员吴顺清为象牙提取提供技术指导,中国丝绸博物馆研究员周旸提前到四川培训考古人员对丝织物残留的寻找。专家咨询团队数十人,国内考古界大佬李伯谦、王巍、陈星灿、王仁湘等在发掘、研究等诸多领域提供宝贵建议。
获邀参与集体攻关的,甚至还有消防科研团队。这是因为三星堆1、2号祭祀坑出土文物有明显被火烧过的痕迹,消防科研团队可以根据出土文物,研究3000多年前的古蜀人究竟是在坑内将文物焚毁还是在坑外点火,当年究竟有多高的温度,才能让不怕火炼的真金也熔化成一团。
本次考古,更像一次多兵种集团作战,称得上一次在全世界也并不多见的世纪考古大发掘。
每一个和三星堆结缘的人都深感自己何其有幸,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党总支书记、院长唐飞也曾语重心长地说:“遇到三星堆,真的是我们三生有幸。”
3号坑“坑主”、90后上大文学院教师徐斐宏也是其中一名幸运者。他是上海人,从小就对文博和考古充满期待和梦想,高中毕业考进北京大学,最初读的是心理学,但学了一年之后,觉得还是放不下心中的考古梦,大二就转到了考古系,一路读到博士。2018年至2020年入选北京大学2016年启动的“博雅博士后”项目,出站后受聘上海大学讲师。
2020年11月,正在山东滕州带着学生做田野考古实习时接到上海大学党委副书记段勇的电话,让他去发掘三星堆的3号坑。这通电话让徐斐宏热血沸腾。他知道,很多考古工作者一辈子都没经历过这样的遗址,这个机会太宝贵了。
图说:青铜神坛(残件)
入坑
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原院长雷兴山调到首都师范大学任副校长,为首都师范大学学生争取到参与三星堆祭祀区发掘的机会。2021年3月28日,在首都师范大学考古系读硕士研究生一年级的刘笑池接到通知时,也感觉像“天上掉了馅饼”,明明前几天自己还是个收看央视三星堆考古直播、隔屏羡慕的观众,现在就要成为亲历者,即将和同学顾旭涛一起前往现场,成为8号坑的一员。
刚到学校报到的刘笑池匆忙收拾了行李,就赶往四川。他在回忆文章中写了初到现场的观感:
“钢结构的考古大棚犹如一个巨大的罩子,将遗址保护起来,为新发现的6个坑遮风挡雨。应急检测实验室、无机质文物应急保护室、微痕物应急保护室、有机质文物应急保护室、文保工作室和考古工作室……现场到处充斥着科技感。”
考古工地一般都在野外,考古工作者风餐露宿,条件极其艰苦,三星堆封闭式考古堪称国内考古界的顶级配置。
刘笑池和顾旭涛参观了当时的考古现场:
“当时的7、8号坑还处在清理填土层的阶段,鲜有文物露头,4号坑覆盖着象牙和黑色的灰烬;然而当我们走到3号坑时,我震惊了:坑内已经清理完填土堆积,目之所及是密密麻麻的象牙和各种文物。大量的象牙交错放置,缝隙处的青铜器虽然还没有完全暴露,但是从数量和体型上已经足以让我感到震撼。那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神秘,更让我充满了好奇与期待。”
此时,3号坑坑长徐斐宏已经带领团队成员发掘数月,他记忆中,2021年春节之前青铜器已经开始露头,3月时埋藏层外露,不断有新发现,提取出来后,下面还有新发现,并且是独一无二的发现。“这是考古里最让人兴奋、向往的部分,很有成就感。”
图说:青铜扭头跪坐人像
兴奋
2021年3月20日至3月23日,央视连续4天直播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考古发掘,各种奇瑰的文物让全国观众使劲儿兴奋了一把。
巨型青铜面具、青铜神树、金面具残片、眼部有彩绘铜头像、鸟形金饰片、金箔、精美牙雕残件、玉琮、玉石器,还有大批的象牙……当时出土的500件珍贵文物和在坑内刚露头只能称为“具有人类形象特征的青铜器”,已经让人激动万分。
3号祭祀坑内,铺满百余根象牙和上百件青铜器,包括青铜尊、青铜罍及独具风格的青铜人像、大面具等;
4号祭祀坑的黑色灰烬中,考古人员提取到了肉眼不可见的丝绸制品残留物,即将采用定制的丝蛋白抗体对灰烬、印痕进行特异性检测,一旦呈现阳性反应,即可初步指认丝绸残留物的存在,再辅以其他检测技术进行确认;
占地仅3.5平方米的5号祭祀坑是最小的一个坑,但出土金器最多,其中一件黄金面具备受瞩目。5号坑还清理出多件金器和60余枚带孔圆形黄金饰片、数量众多的玉质管珠和象牙饰品。经专家初步判断,这些有规律的金片和玉器与黄金面具形成缀合,推测为古蜀国王举行盛大祭祀仪式时所用;
6号祭祀坑发现了一具“木匣”,长约1.5米、宽约0.4米,内外均涂抹朱砂,具体功用还需进一步研究破解。
徐斐宏说,虽然对三星堆有预期,但还是有太多让人意想不到的东西。当时的7、8号坑还在发掘填土阶段,再后来,一件接一件的出土文物没有最怪,只有更怪,以至于专业人士一时都无法界定一些器物的属性,年轻的考古队员趣称它们为“奇奇怪怪、可可爱爱”,把酷似卡通形象的神兽称为“机器狗”。
图说:陶猪
考古
这次三星堆考古,各种纪录片和直播节目让人们看到了很多考古工作中的实况。在纪录片《不止考古·我与三星堆》中,不时能听到队员们“我的老腰都快断了”“太费腰了”的感叹,考古队员每天要趴在吊在坑上的工作台上,用腰和颈椎撑着身体,双手探到坑里,一点点剔掉器物旁边的泥土。8号坑坑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赵昊和队友在发掘大口尊时,两个男队员趴在工作台上,四手合抬,使出浑身的力气,憋出了闷哼,它也纹丝不动。
纪录片中稍带戏剧化、趣味化的表现,多多少少遮掩了个中的艰辛,事实上考古依然是个辛苦不足为外人道的工作。看似可以寄情山水,呼吸新鲜空气,触碰别人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国宝。但使用牙签和勺子将一坑填土一点点挑起的重复和枯燥不仅常人难以忍受,长年累月生活在外地的孤独滋味也是一杯难饮的苦酒,挖掘的过程也并不总有新的发现,很长的时间伴随着他们的是焦虑与失落。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工作队的乔钢在三星堆工作了十余年,片中对他一天工作的描述直白地呈现了考古工作的真实:“寻常地上工,寻常地挖土,寻常地划线,寻常地——一无所获”。
7号坑坑长、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黎海超面对的7号坑,和其他坑最大的不同是坑里看不到完整的器物,只有一地碎片。有时候,黎海超会去旁边的3号坑、8号坑串门,看着别人坑里露头的一个屁股朝上穿着超短裙的青铜小人、一个当时造型奇特精美的青铜神坛,心里多少有些失落。
好在苍天不负,2022年6月,一个龟背形网格状器的露面,让黎海超这么多天的坚守有了回报。这件龟背形网格状器有上下两个网格,中间包裹着一件打磨精细的玉石,四个角有四个龙头的锁扣,非常漂亮。后来又在它身上分别发现了黄金和丝绸残留物,说明当时的三星堆人把他们所能获得的最珍贵的东西全都包裹在了这件器物上。本轮三星堆遗址祭祀坑考古发掘特约摄影师余嘉这次拍了三星堆不下10万张照片,这件网格器让他觉得,它就是所有文物中的“老大”。
记录
余嘉是考古现场一个特殊的人物。队员们和他还不熟的时候,会问“那个整天背着包在坑里转悠的人,是干啥的”,后来余嘉和坑里每个考古队员都成了朋友,成了他们口中的“嘉哥”。
他现在的职务是广汉图书馆馆长,中国国家地理的签约摄影师,地道的广汉人。和三星堆最早的接触始于1997年三星堆博物馆老馆开幕,那时候他还是个20岁不到的小青年,后来因为自学摄影,表现出不凡的天赋,受邀为三星堆拍摄新闻图片。他拍的照片很美,很多人也因此喜欢上三星堆。
这一次,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想找一位有人文情怀的摄影师,来记录考古过程和出土文物,余嘉经三星堆博物馆老馆长肖先进推荐入选。
当他的双脚第一次踏上坑中几千年前的泥土时,心中莫名感到一阵敬畏,“真的能感觉到,好像坑上有很多人在忙碌,不是扔,是慢慢地在传递,将器物一件件摆放进坑中”。
余嘉拍了很多器物,发现它们最好的一面都朝上,圆口方尊下面已经锈烂,向上的却是完好的,顶尊跪坐人像也是很安详地躺在那儿。从镜头里看出去的时候,余嘉经常会想,是不是安放的人就想着,终有一天会有人看到。
入坑拍摄的一年半时间,余嘉基本不出差,就怕错过了什么。和坑里的考古队员熟了,提取重要文物的时候都会通知他一声。2021年6月23日,他接到徐斐宏的电话,说青铜大面具即将提取。当时他正在10公里外的地方办事,挂了电话立即驱车赶往三星堆,一路想的全是拍摄要用的镜头和光圈,一下车,就立即套上防护服下坑。
“30厘米、50厘米……”当青铜大面具被提到一人高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中心文物修复师任俊锋正好抬眼看向大面具,余嘉毫不犹豫地“咔嚓”一声,定格了这张“跨越3000多年的凝望”。
时间长了,坑长和队员都懂了他的摄影语言,尽最大可能配合他拍出最好的角度,呈现出文物最深的内涵。“让文物会说话”,让公众看得懂文物,能够感受、理解文物所传递出的复杂信息,才能让考古工作的价值得到最大的呈现,才能让文明的印记刻在人们的心中。
修复
三星堆祭祀坑新一轮考古发掘中,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共出土编号文物17000余件,较完整器物2400余件(约14%),其中包括顶尊曲身鸟足铜神像、兽托顶尊跪坐铜人像、龟背形网格状器、铜神坛、铜神兽、鸟形金饰片和金面具等重要器物。大量残缺、开裂、变形、腐蚀严重的出土文物需要及时进行清理、拼接、整理和保护修复。
提取出的文物送到三星堆文物保护与修复馆,与坑里欢声笑语的气氛不同,修复室里总是一片寂静,修复大师们都默默做着手头的活,需要沟通的时候也就寥寥。
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金石修复组的修复师金大朝说,三星堆的青铜器不属于典型的青铜器类型,对修复人员来说,最大的压力就是探索过程中遇到的未知,所以必须非常专注,一旦发现了非常规的状况,马上要做出判断。三星堆不少文物带有彩绘,他清理的一件原本被判定没有,但当他慢慢清理掉薄薄的泥土层时,突然发现了下层中的彩绘,若不够专注,很可能会错过。
三星堆文物的修复故事,和考古故事一样,三天三夜也说不完。第一代文物修复大师杨晓邬和弟子郭汉中的故事,早已被传为业界内外的美谈,杨老当年不拘一格降人才,将心灵手巧的农家少年郭汉中收入门下,师徒俩花费10年,修好了三星堆1号神树。如今,身为三星堆博物馆文物保管部副部长的郭汉中已荣膺“大国工匠”的称号,他又将一身的技艺传授给徒弟余健和谢丽。
在馆外,还有一位罕为人知的陶器修复民间大师曾卷炳,由于不少三星堆的陶器修复论文中都有他的名字,三星堆的考古人员都尊敬地称74岁的他为“曾院士”。曾爷爷是三星村的农民,40岁起就跟着三星堆考古队干活,除了修陶器,有时候还会跟随考古队出差,做文物调查。
不出差的时候,曾爷爷一有时间就骑着他的小电驴,到老的三星堆工作站工作。一堆破陶片,曾爷爷一眼就能看出颜色、质地和弧度的关系,一片片对比着茬口,拼接在一起。他最得意的一件修复作品是三星堆挖出的一个大陶罐,仅存直径20多厘米的罐口、一点点底部和拼接出的一条罐身,最宽的地方不过七八厘米。曾爷爷花了好几天工夫,用石膏根据残片的弧度,一点点将整个大陶罐修补完整,现在这只大陶罐已经摆放在三星堆博物馆新馆的展柜里。
新馆
2022年11月9日,三星堆考古封坑仪式悄然举行,喧闹了两年多的考古工地再度沉寂。而大约1公里外的三星堆博物馆新馆正在紧锣密鼓地兴建,今年7月27日面向公众试运行。早已被各种直播和视频吊足了胃口的人们蜂拥而至,一睹上新的文物。
新馆展品除1、2号祭祀坑出土的文物外,还陈列展示了新一轮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共展出陶器、青铜器、玉石器、金器、象牙(含象牙雕刻)等各类文物共1500余件(套),数量为原展出文物的3倍有余,近600件文物初次展出。
在新馆中,还有3组实现了“历时三千年 跨坑重聚首”的特殊文物。
第一组是青铜神坛,主要由8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神兽、上有13个小型青铜人像的镂空基台,3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顶坛人像、青铜持鸟立人像,7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顶尊跪坐人像,以及2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顶尊跪坐人像拼合而成;
第二组是青铜鸟足神像,由8号、3号和2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罍、青铜顶尊神像、青铜鸟足人像、青铜鸟足人像、青铜龙形器盖、青铜持龙立人像、青铜杖形器拼合而成;
第三组是青铜骑兽顶尊人像,由8号、3号、2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神兽、青铜骑姿顶尊人像、青铜尊口沿拼合而成。
这3组文物采用“数字化修复演示”的展陈方式,借助修复师的手工拼对结合AI算法,通过数字化虚拟修复技术实现器物的跨坑拼接及修补复原,并通过3D打印技术制作出原比例研究性复原的仿制品,重现文物神采。
刘笑池说,在发掘时考古队员就已经有意识去跨坑比对有关联性的器物。青铜神坛上部的主要构件就是在3号坑刚发现时被称为“奇奇怪怪”的文物,而8号坑发现小型顶尊跪坐人像时,赵昊等考古专家即指出可能是神坛上面的,刘笑池还特意取了7号坑的器物与8号坑未提取的器物比对过。最后在2、8、7、3号坑分别找到一个小型顶尊跪坐人像,与下方青铜觚顶部的4个口部对应上。
造型奇特的“上新”文物丰富了三星堆遗址的铜器类别,呈现出更加丰富的种类和文化内涵,但“其想象体现出的内心世界是中华文明‘天人合一、万物共生’的和谐理念,与中华其他区域文明对世界的想象高度一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说。
申遗
绵绵细雨中,从祭祀坑向东北穿过马牧河,穿过田间绵延的小路前往博物馆,沿途经过当年最初发现三星堆玉石器的燕家院子和被树丛密密掩盖的三星堆西城墙遗址。两侧稻田一片青翠,8月的稻谷已然吐穗,像是在预祝今年的丰收,阡陌间时而飞起几只白鹭,让人油然而生穿越感——3000多年前的古蜀人,看到的应是同一番景象吧?
三星堆—金沙遗址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正在进行中,两地是古蜀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延绵不断”的重要实证,对于研究文明起源多元性和古代城市发展具有重要价值。2023年3月,三星堆管委会已邀请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赴三星堆遗址实地调研,指导开展申遗工作。
考古的结束和新馆的开启只是一个段落,考古发掘工作仍然在推进。下半年,三星堆遗址月亮湾考古发掘将继续进行,要理清大型建筑基址面貌;三星堆古城南部考古试图寻找聚落,为完善研究三星堆文化社会结构提供新的思路;仓包包小城考古勘探工作推进,进一步理清古城内小城结构和功能。其他东、西、南城墙、青关山建筑基地保护展示项目、马牧河、鸭子河环境整治,恢复历史风貌等都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中。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郝爽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要有突出普遍的价值,真实性和完整性,以及运转良好的保护管理体系作为支撑。未来三星堆不仅要在博物馆里展示遗产的价值,还要将祭祀遗址本体以及祭祀活动在三星堆崇高的地位呈现出来。三星堆有内外城,1-8号祭祀坑是在内城城墙边缘的位置,是整个城池地势最高的台地上,这些信息都要通过遗址的现场展示让观众完整、直观地感受到。
郝爽最期待将来的考古发掘能够探明作坊区和贵族墓葬区的位置,这些新的考古发现也会使三星堆的突出普遍价值更有说服力。
相信未来的三星堆遗址公园更能够清晰地展示出中华文明先民的生活痕迹。10万余张照片中,余嘉雪藏了一组非常特殊的作品,拍摄对象是考古坑中的青铜人像揭去之后,在泥土上留下的清晰痕迹,那是古蜀人跨越了3000年的时光,留在人类文明中最为深刻的印记。
新民晚报特派记者 姜燕
标签: